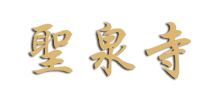
编辑:九华山圣泉寺-九华山聖泉寺
走进寺院,不可忽视的风景之一,就是门楣梁柱间的匾额抱联。过去人很讲究,往往从这些文字内容,便可一窥家风。
士夫阶层尤喜访寺寻僧,参禅悟道。譬如大文豪苏东坡,一生接游的僧人少说也上百,造访的寺院不计其数。他与佛印了元禅师的交往,始自被贬黄州的岁月。某日,东坡做了首偈子,“稽首天中天,毫光照大千。八风吹不动,端坐紫金莲”,自觉快意,便差人呈给江对岸的了元禅师,禅师速回二字:放屁。东坡一看,当即渡江来,问禅师何以秽语相加。禅师大笑:“八风吹不动,一屁打过江。”
千载之下,读者无不忍俊抚掌,为着禅师的信手拈来与坡仙的率真。倏尔回味时,又犹如棒喝加身。
相较之下,黄鲁直则显露出士人参禅独有的优美与文雅。彼时黄庭坚拜师晦堂门下,正值秋空霁海,师领弟子行于深山,忽顿足问曰“闻木樨香否”,鲁直不假思索“闻”,禅师瞪眼:“吾无隐乎尔!”黄鲁直言下有悟,随即写下诵偈:昨夜月明云散后,西风一树木樨香。
迄今,苏州留园还有一座亭子:闻木樨香轩。番禺余荫园亦存闻木樨香否的匾额。足见后人对一抹智慧之香,念念不忘的心情。
唐人笃信佛法,比起宋人有过之无不及。出于对维摩诘居士的追慕,王摩诘毕生熟读净名经,戒杀茹素,不衣文彩。尤喜与自己性情吻合的禅宗,每每焚香静坐,必以禅诵为课。故而观其诗文,无不浸透着禅的空灵闲寂,一派平和之境。
若论禅净双修,当首推香山居士。香山居士信仰虔诚,自少年始便栖心释梵,通学佛乘,深入经藏,依教奉行,直到终老。细品其而立之年所作的八渐偈,足见其一番定慧功夫。人生迟暮的一首《念佛吟》,则是他求归弥陀净土的愿力所在。
余年近七十,不复事吟哦。
看经费眼力,作福畏奔波。
何以度心眼,一声阿弥陀。
行也阿弥陀,坐也阿弥陀。
纵饶忙似箭,不离阿弥陀。
达人应笑我,多却阿弥陀。
达也作么生,不达又如何。
普劝法界众,同念阿弥陀。
这些惊才绝艳的大丈夫,何以纷纷走向寺院,为佛法所折服?
人间底色不过悲欢离合,生命基调无非生老病死。正如金刚经中六如偈所表,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,如露亦如电。或似净名经所言“是身如芭蕉”“是身无主”…
说到底,佛法是纯粹心灵的宗教。
倘若人的心念有其实体,那么整个一生的念头堆起来,恐怕要堆满须弥峰且不止。无论多高明的士人、艺术家,政客、商贾,或是农夫走卒,都是“千山易过,难过一念”。
当遍历得失毁誉,初生的腾跃转瞬成空,不可能完 美的生命本质乍现眼前。佛法说,法尔如是。
本来无常,诸法因缘生,诸法因缘灭。梁武帝来了,是这样,乞丐来了,还是这样。佛法慈悲,慈眼视众生,普照尘世间的每一桩生命,启其慧命,远离颠倒梦想,超脱种种“名”的分别,回溯生命本来的空灵与寂静。身如芭蕉,心似莲花。
不染于物,无缚于尘,清净调柔,随缘应世,纯粹的生命的解脱,不啻为无上的人文情怀。
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,三宝住持的寺院却历久弥新。寺里的那些菩萨塑像从未有过只言片语。可在那亘古的默然间,在出尘的微笑里,每个走进来的人,都能谛观自身心中的答案。
